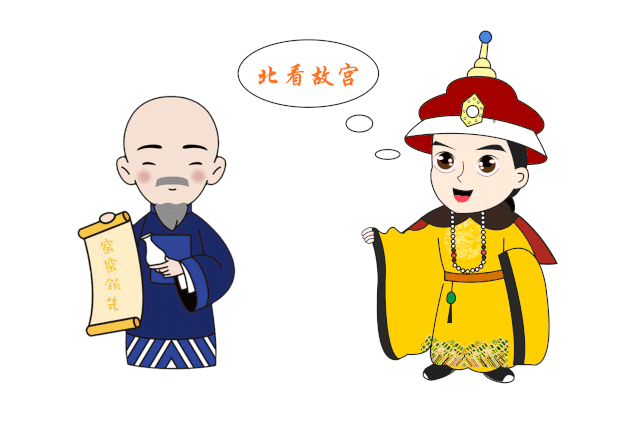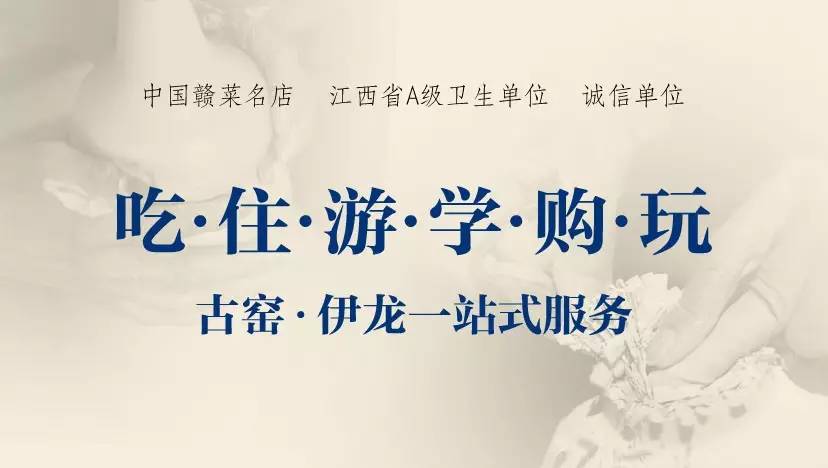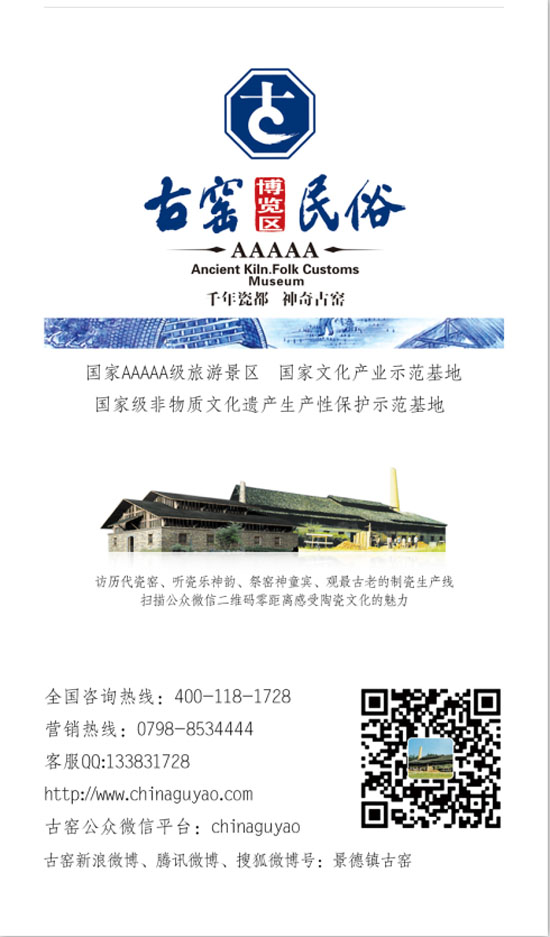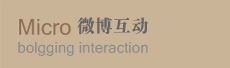【古窑讲堂】阎崇年:大故宫《御窑千年》(六)设博易务之首任税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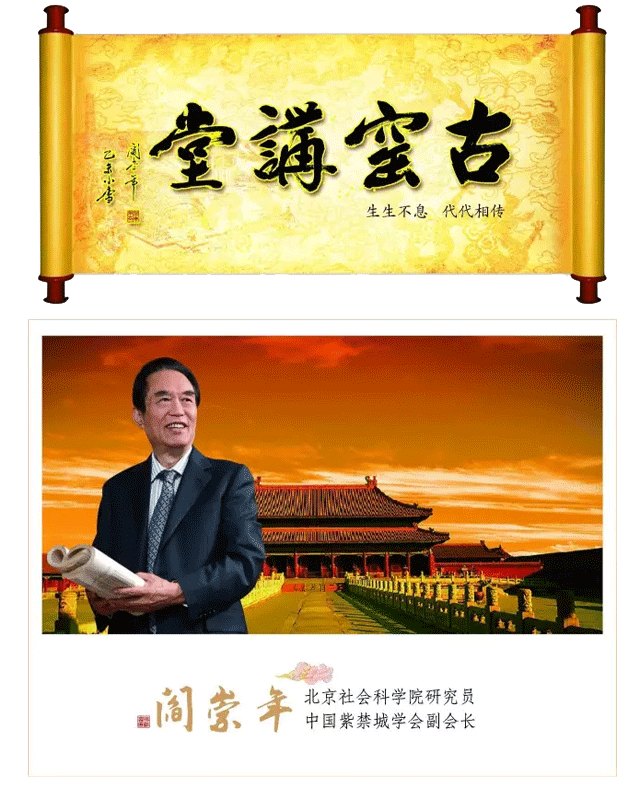
在景德镇设置瓷窑博易务,提出建议并首任税官的是余尧臣。
余尧臣,韶州曲江(今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)人,是名门之后。他的祖父余靖(1000-1064),字安道,天圣二年(1024)进士,时年二十五,《宋史》有传。余靖中进士后,经过十年历练,仕途迎来转机,进京任职,校勘古籍,展露才华。范仲淹上书批评宰相吕夷简,结果被贬到江西,知饶州。余靖的官位还没有坐稳,因替范仲淹说话,也被贬谪出京。庆历年间,宋仁宗实行新政,范仲淹主持。余靖和欧阳修、蔡襄等担任谏官。余靖得到仁宗信任,经常面圣,直言不讳。据说,余靖不修边幅,盛夏入宫,力谏不休。一次,仁宗总算打发他走了,对身边人说,自己“被一汗臭汉薰杀,喷唾在吾面上”。皇帝能宽容臣下到这种程度,也不容易。然而,几年后,范仲淹失势,余靖也受到牵连。他上疏:“陛下自亲政以来,屡逐言事者,恐钳天下口,不可。”疏入,余靖遭落职,被贬出京城,客死于秦亭(今南京秦淮亭)。这里有个故事,史载:“靖尝梦神人告以所终官而死秦亭,故靖常畏西行。及卒,则江宁府秦淮亭也。”
时过境迁。余靖的孙子余尧臣时任宣义郎、都提举市易司勾当公事。“市易司”就是前面说的执行王安石“市易法”的机构。余尧臣在市易司任职,积极推行“市易法”。他认为景德镇陶瓷贸易繁盛,国家如果参与进去,不失为一大财源,所以提议在景德镇实行“市易法”,建立“瓷窑博易务”。不仅如此,朝廷还让余尧臣负责瓷窑博易务工作。万事开头难,余尧臣奋斗了一年,“方且就绪,以勤官而死”,竟然累死在任上。
余尧臣因公殉职。他的弟弟余舜臣当时也在饶州做官,上疏请求接替哥哥之职,颇有几分前仆后继的悲壮,不过没有获得批准。事实上,虽然余尧臣积极参与变法,又死于职守,朝廷却从未旌表过他,甚至历史记载都非常稀少。究其原因,大概和“市易法”本身存在争议有关。“市易法”虽然设想很好,执行起来却走了样。
一是,国家做生意,为了赚钱,官员倚仗权力欺行霸市。
商旅所有者尽收,市肆所无者必索,率贱市贵鬻,广裒赢余,是挟官府为兼并也。
这显然比囤积居奇的大商人还坏。
二是,国家为赚利息,放高利贷。说来说去,还是赚钱心切,顾不上老百姓的利益,本以为可以利国利民,却导致与民争利,可谓适得其反。
好心办了坏事,事情的首议者、实际的推行者,难免要挨批评。大文豪苏轼就曾经批评过余尧臣:
扬州芍药为天下冠。蔡繁卿为守,始作万花会,用花十余万枝,既残诸园,又吏因缘为奸,民大病之。余始至,问民疾苦,以此为首,遂罢之。万花本洛阳故事,亦必为民害也,会当有罢之者。钱惟演为留守,始置驿,贡洛花,识者鄙之,此宫妾爱君之意也。蔡君谟始加法造小团茶贡之,富彦国叹曰:“君谟乃为此耶!”近者余安道孙献策榷饶州陶器,自监榷,得提举,死焉。偶读《太平广记》:贞元五年,李白子伯禽为嘉兴乍浦下场杂盐官,侮慢庙神以死。以此知不肖子,代不乏人也。
在苏轼看来,蔡繁卿、钱惟演、蔡襄(君谟),特别是余尧臣从景德镇瓷窑中为国取利、聚敛民财、谄媚圣上,小民受害,实不足取。苏东坡大概实在生气,竟然把余尧臣殉职和“侮慢庙神以死”相提并论。“市易法”遭到一些人仇恨,自然推行不了多久。宋神宗一死,人亡政息。余尧臣的事迹,也和瓷窑博易务一道,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。
北宋时,先后有两次大的新政运动:一是宋仁宗朝的庆历新政,主要由范仲淹主持;二是宋神宗朝的熙宁新政,主要由王安石主持。余靖、余尧臣祖孙,分别是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政的参与者。仕途艰难,变幻莫测。新政变法,宦海风浪,既生机遇,更伏凶险。余靖、余尧臣祖孙,投入变法漩涡,忽而跃上潮头,忽而跌人浪谷。他们的际遇,既令人叹惋,也引人深思。
下面介绍两位景德镇镇监,即莫濛和罗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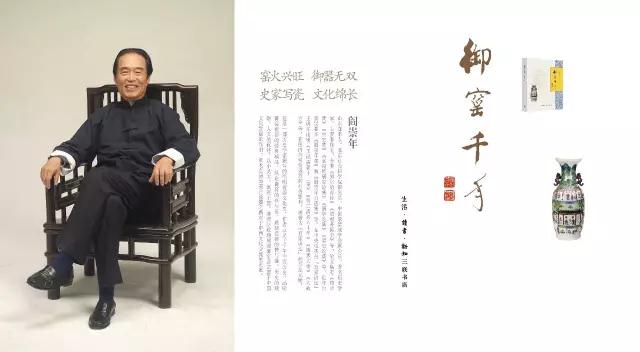

执行:一把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