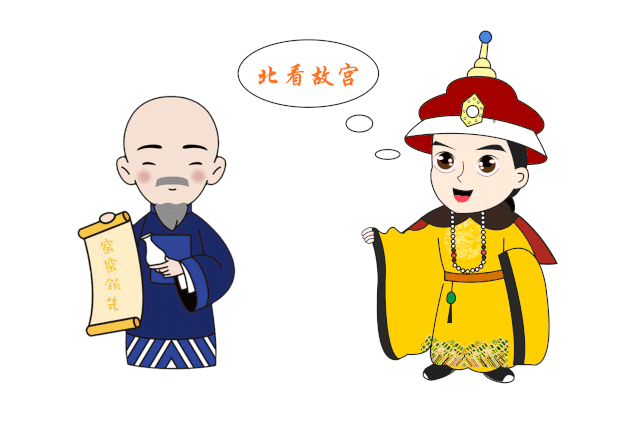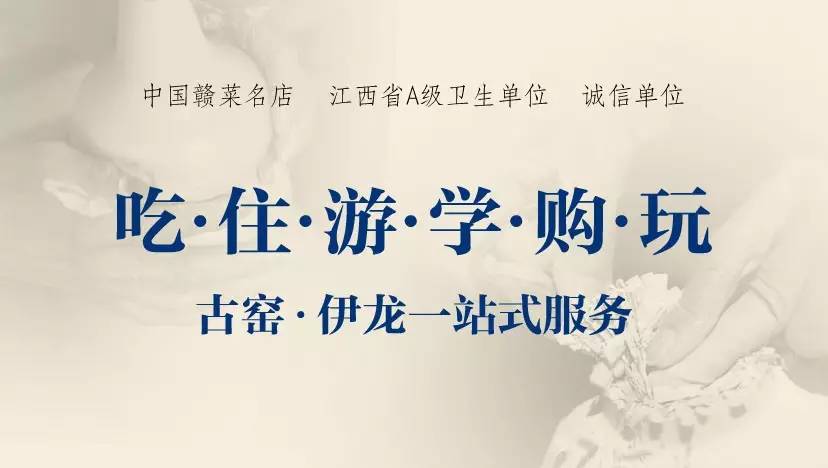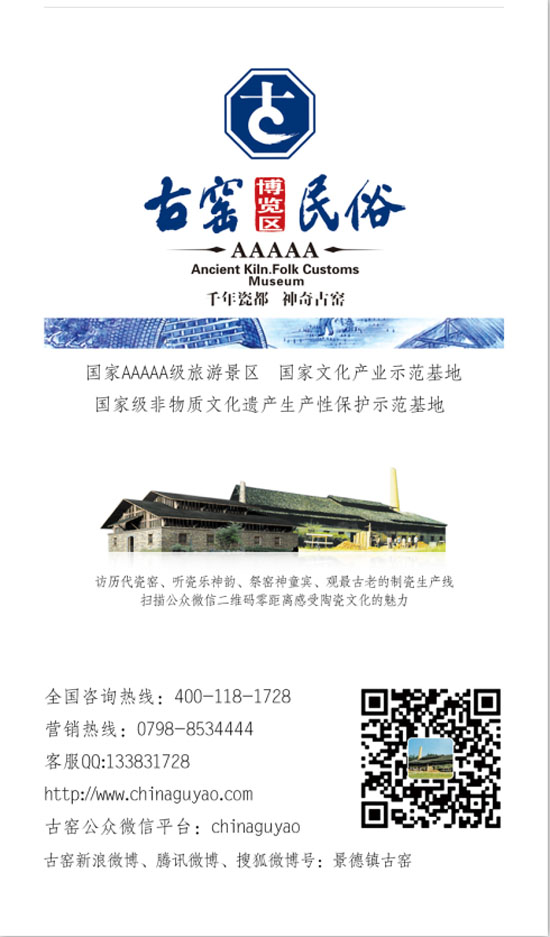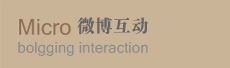【古窑讲堂】阎崇年:大故宫《御窑千年》序(四)御窑之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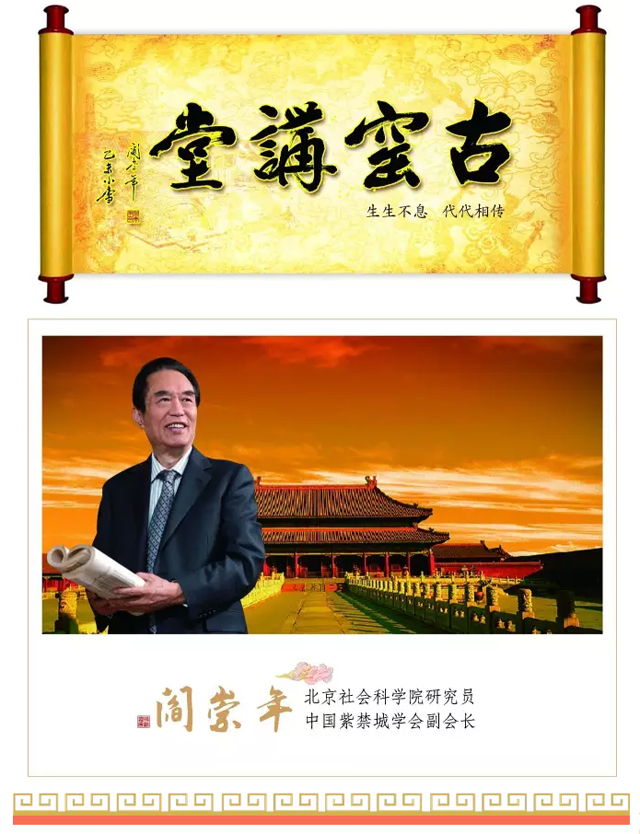

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云:“济济多士,文王以宁。”御窑瓷器,重在得人。
探索御窑的历史,既要重器,也要重道;既应重物,更应重人。瓷人,为御窑烧造瓷器,献出了汗水、心力、智慧和生命。“窑神”童宾是其英烈,“瓷神”唐英是其英杰。唐英为人——“未能随俗惟求已,除却读书都让人”,唐英为官——“真清真白阶前雪,奇富奇贫架上书”。这是真的心扉,善的心灵,美的心境。唐英,不幸也奴仆,有幸也奴仆。他之不幸,出身奴仆,没有享受八旗特权,而任劳、任怨、任贫、任贱,与工匠“同其食息”;他之有幸,出身奴仆,没有成为八旗子弟,而善书、善画、善艺、善陶,被誉为“陶瓷神人”。御窑历史,笔者做出评价:御窑千年史,唐英第一人。从瓷器历史来看,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,还是在当时的世界,都能站在引领瓷器潮流创新的前沿者,唐英当之无愧。因此,不仅在中国瓷器史上,而且在世界瓷器史上,唐英都应当有着自己的历史地位。
在这里插一段闲话。我同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的联系已经14年。关于与观众、听众的关系,从演讲的人来说,应当努力追求“四个明白”:一要“学明白”,就是自己要把讲的内容弄明白,不能“以己昏昏,使人昭昭”;二要“写明白”,自己心里明白,不一定能用文字表述明白,所以讲稿要尽量写明白;三要“讲明白”,写明白不一定能讲明白,要力求讲得雅俗共赏,事理圆通;四要“听明白”,就是自己觉得讲明白了,但观众、听众往往没有看明白、听明白,要根据大家的反应,把问题讲清楚。所以,学明白、写明白、讲明白、听明白,应是一位教师、一位讲者,对观众、听众、读者、网民所应当细心体察、热心关注的目标。
回过头来说本书。《御窑千年》不是一部陶瓷史,而是探讨宫廷与御窑瓷器的历史与文化之关系,选择明清故宫存量最多、档案记载最详、文献记述最丰、社会影响最大的御窑瓷器为重点,难免有以偏概全、顾此失彼之虞。瓷器之选择,以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沈阳故宫博物院、南京博物院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、高安博物馆的藏品为主,酌予兼收其他博物馆的珍藏。
本书分为四个单元、共十六讲,即宋代两讲、元代两讲、明代五讲、清代六讲,最后以“瓷器之路”一讲为结尾。本书插图137幅,尽量选择有代表性的、博物院(馆)收藏的、宫廷旧藏的、极其精美的瓷器照片,图随文走,以供赏阅。
最后,经过三年多的学习与思考、构思与撰著、编辑与出版,《御窑千年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。考卷算是交了,心力算是尽了,分数是多少?成绩又如何?借用佛家的话收尾:“只结善缘,不问前程。”
是为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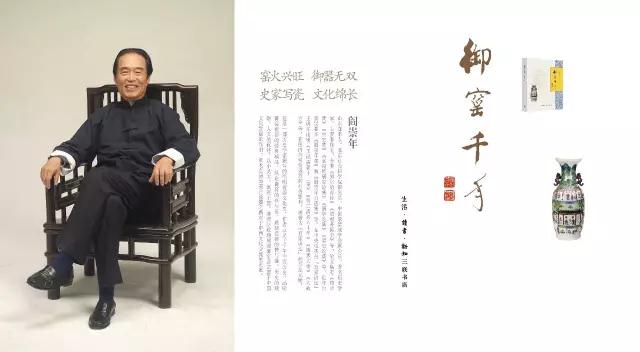

执行:一把火